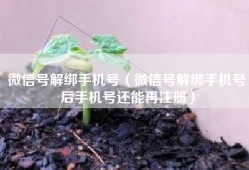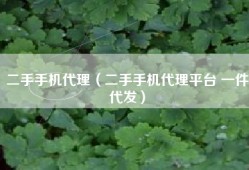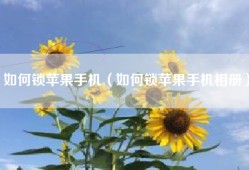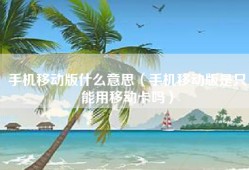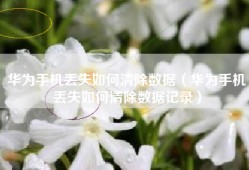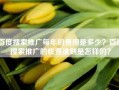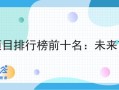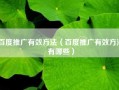【原】《汉魏六朝诗选》第七十四首《咏史八首》
- 资讯
- 2025-02-22
- 61
壹/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佚名
贰/
《咏史》作为一类诗歌题材,以班固的《咏史》诗为出现的标志,其后王粲、阮瑀写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文选》第二十一卷收录的咏史题材的诗就有二十一首。然而左思凭借着其八首《咏史》诗名垂青史,获得“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诗薮·外编》卷二)的美名。这一方面是因为左思高超的写作技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诗歌作为咏史诗的变体,突破了原有的班固《咏史》诗的正体的局限,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平衡了诗歌的史意的关系,使咏史诗有向咏怀诗靠拢的趋势,打开了咏史诗的境界。
(一)左思的《咏史》中史与意的结合方式。
清人张玉谷在《古诗赏析》中评左思《咏史》八首史事和抒情结合的不同方式时云:“或先述己意,而以史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和,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下面我们将结合八首诗作具体分析。
其一: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本篇为第一首,乃是言志之作,表明自己愿意为国立功和功成不受爵的抱负。诗的开篇展示了诗人少年博览群书,接着,又说自己虽然不是军人但熟读司马穰苴兵书,肯定自己文武全才。当他为国立功后却又“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本诗正是体现了“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全诗并未直接提及具体的史事,而是通过叙述自己的才能来表达“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心志。而在提及自己的才能时,左思以贾谊、司马相如自比,“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可以看出左思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负,他梦想能够像贾谊、司马相如二人样得到赏识和重用,施展才能,实现抱负。
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第二首较之于第一,情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已无其一的自信昂扬之情。作者“先述己意,再以史证之”。开篇用比兴,对比的手法揭示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现象,激烈的抨击了门阀制度对人才的压抑,倾诉了贫寒之士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的社会现实。至此,左思以形象的语言,有力地揭露了门阀制度的弊端。紧接着,以金张、冯唐为证,抨击了埋没人才的门阀制度的不合理现象,“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作者看似为冯唐鸣不平,实际是以冯唐自拟。并且,左思此诗中的所思所感并非其一人控诉,代表了一代寒士们长久陈郁心中而不得不吐露的心声。
其三: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连玺曜前庭,比之犹浮云。
其三的史意结合方式较之于前两首有所不同。“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诗篇开头即用“吾希”“吾慕”对段干木、鲁仲连二位历史人物发表议论,直接表露对历史人物的崇敬之情,实现了“史意相融”。接下来,作者记述段干木、鲁仲连“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连玺曜前庭,比之犹浮云”的历史事实,歌颂二人在国家遭遇危难之际从容不迫、排难解纷,却又不受爵禄、功成辞赏的精神,表达诗人对前人的向往和为人的钦佩。同时,不难看出,作者将段干木、鲁仲连视为自己的模范和行为准则,暗含了他愿意像这二位历史人物一样身体力行实现立功为民的理想及功成身退的淡泊之志。关于这一层思想感情,作者并未像表达赞颂之情一样直接坦露,但是做到了“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
其四: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其四采用了对比手法,前四句即生动的描写了王公贵族的奢靡生活;“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紧接着描写了扬雄闭门著书的寂寥生活。作者又以扬雄自拟,他与扬雄的相同之处在于出身寒微,却都刻苦勤勉,富有才能,却并未如他一样“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表达了作者的苦闷。全诗未提及本人意志,但是通过对比,间接而又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想法,实现“止述史事,己意默寓”。
其五: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咏史》其五,开篇写宫殿的高大、密集,但在这高大密集的宫殿里皆是王侯,诗人自己却无法跨进那个门。“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两句直接抒情,说自己不是追随帝王将相以求功名利禄之人。接着诗人暗用“被褐”典故和传说中的隐士许由不受官的史事,抒写自己高蹈遗世的志向,这是理想遭到现实嘲弄后的反弹。从以上分析中,我们认为这符合张玉谷“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的观点。
其六: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咏史》其六,“荆轲饮燕市,哀歌和渐离”的历史情景写出了荆轲、高渐离藐视四海,睥睨豪右的英雄气概。“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来说明他们不同于一般人。此时作者已不仅仅是写历史上人物的态度,而是把自己这个抒情主体与历史上人物的情感态度融合,作者的感情与他们的感情相通,从而抒发了自己对权贵豪右的蔑视。诗人由引出历史人物到展开议论,再抒己志。我们认为这符合张玉谷的“先述史事,而以意断之”的这一观点。
其七: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咏史》其七,诗人用平铺直叙的手法写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这四个有才之士在未被重用之时遭遇困厄的故事。前八句诗中暗含着自己怀抱奇才而被遗弃的慨叹。后八句又抒写自己的感情,诗人似乎发现一个规律:英雄遭遇困厄,自古就是这样,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有被遗弃的奇才。这也是诗人的一种之情。先举史事,再抒己情,我们认为张玉谷“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这一评论凝练准确。
其八: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咏史》其八,前六句是诗人自己晚年退居洛阳宜春里,专思著述的生活写照。“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写出了生活的贫苦。接着他以历史上苏秦和李斯的例子来印证祸福之理,慨叹他们不安贫贱终致罹祸。诗人的选择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超脱,也是基于现实出发。
这时诗人的感情已不像前七首那样积极进取,悲愤不平,而是转向一种知足常乐,安身立命之情。我们认为这首诗作者是先述己意,以史证之,再结合史事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感情。
(二)左思《咏史》的情感脉络
纵观八首诗,始于“铅刀貴一割,梦想骋良图”,终于“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从少年意气,挥斥方遒;到屡屡碰壁,无奈妥协,但仍希望得到赏识,实现抱负;最后到完全绝望。这是左思的一生,也是西晋门阀制度下寒门士子的一生,才质高洁,却只能沉沦下寮;志存高远,却只能屈居小吏,最后带着对时代的失望与悲哀走向超脱,这种超脱是假超脱,是不得已的时代所能做出的唯一保存自己的选择,如果不想最终回首向来萧瑟,惊觉物是人非,人事寥落,只能默默退守,去谱一曲山水歌谣,回归心灵的宁静。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一首,抒不尽的昂扬士气,荡不去的豪情满怀,那时的左思,未经风雨,天真地认为这个社会会回报给他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功成名就之后的结局都设想的如此美好,“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少年的畅想,天真的可爱。
然而很快,现实的残酷张开了獠牙,这个吞没了无数个才能卓越的高洁之士的社会制度,又怎么可能为左思而例外?“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现实早就由来已久,品质卑劣的世族子弟恩荫祖上,无数寒素之士只能被这些纨绔阻挠,毫无出路。左思满怀愤怒,控诉着社会的不公,这时的他,仍旧怀着高涨的热情,正因为还对这个社会抱有幻想,所以才会爱之深,责之切,希望能够有所改变。
在控诉社会的不公之后,左思已经开始对于入仕不再抱有幻想,转而希望能够以白衣之身报效国家,他以段干木、鲁仲连为喻,仍旧希望能够完成修齐治平的理想。此时的他,对于功名利禄,蹑居高位已经看得极淡,“不义而富且贵,于他已如浮云”。
然而就连这样的不计名利的抱负都无法实现,左思与那些富累王侯的世家同住于济济京城,世家大族冠盖满京华,过着奢靡不堪的生活;而真正想要做些对国家有益之事的自己却门前冷落鞍马稀。左思空有超拔才能,却只能寄希望于百年之后,可以有后人发现自己曾经的才能,曾经的抱负,曾经的品格。
随着时间的流逝,左思已经愈发感到悲哀,他甚至开始忿恨自己,为什么要到京城来呢?只能白白的失望罢了。“自非攀龙客”的身份定位让左思开始质疑自己当年的选择究竟是出于钻营还是志向,最终他决定效仿许由,抛弃一切,只为得到真正的自由。
临走之前,左思想到了荆轲,他地位可以说是卑贱的,但是灵魂却高贵,相比于那些自命不凡的王侯,哪怕自矜功伐,也不过是历史的尘埃,而真正的高洁之士,最终会得到重若泰山的评价。
左思在反思自己为何无法成就功名的时候,发现除了社会制度不给他机遇之外,他缺少伯乐知己,正如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分别有着卫青、严助、魏无知、杨得意的赏识一样,左思也在渴望着一个伯乐,一个能够聆听自己的子期,然而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在最后的最后,左思已经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士子,而是一个困居俗世,在希望与失望之中无法挣脱的笼中囚鸟,世事变化无常,荣华腐朽都不过一瞬之间,为什么还要死守着所谓的志向抱负呢?但愿能够栖身山林草泽之间,可以成为隐士的楷模。
西晋是一个可怕的朝代,所谓的魏晋风流的繁华气度下掩盖着极为悬殊的社会现实,高门大族与寒素之士,这个社会最终也没有给左思,给无数个像左思一样的人们一个机会。《咏史诗》的背后,是一个悲伤落寞的诗人的一段悲伤落寞的故事。
(三)左思《咏史》对咏史题材正体的突破
清人何焯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抒胸意,乃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刘学锴也将左思《咏史》的咏怀与前人的咏人、咏事相区分(《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
佚名
叁/
一、文才武略思报国 《咏史八首》其一: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左思能文能武,说到文才,著论达到《过秦论》的水准,作赋可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相比拟;说到武略,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他有报国的才干,有以安邦定国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他满怀文才武略,期望为国建功,并不贪图封赏。
二、门阀制度挡住了多少报国的脚步啊! 《咏史八首》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左思有文才武略,但因出身寒微,仕途坎坷,不能施展抱负,因此愤懑不平。那么,是什么挡住了左思报国的脚步呢?是门阀制度。也就是诗中所说的“门阀”。 三、只要国有贤人,国君又能礼遇贤人,敌人就不敢轻易来犯啊! 《咏史八首》其三: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左思认为,只要国有贤人,国君又能尊敬、礼遇贤人,就能受到人民的拥护,敌人就不敢轻易来犯。自己愿意为国建功立业呀,而功成之后,却不愿意受封赏。
此言此语,读来令人唏嘘。自古以来,有明君思贤若渴,有昏君弃才不用;有小人占据高位不思报国,有志士一腔热血报国无门!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啊,怎样才能繁荣富强;我们那热爱祖国的人民啊,如何才能幸福安康!纵观历史,我们从来不缺贤良之士,更多的时候,我们缺的是贤良的领袖和好的制度啊! 四、杨雄著书百世流芳,权贵淫乐致国灭亡 《咏史八首》其四: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 左思认为,西汉的统治者不以国事为重,整日纵欲淫乐。社会的必将导致国家的灭亡,权贵们也会随着国家的灭亡化为埃尘。而杨雄安于贫困,著书讲学,成就辉煌,英名流芳百世。杨雄是他的楷模,左思找到了希望,他会成为杨雄那样的人物而流芳百世。诗读至此,不由想到古人常说的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而兼济天下。这句看来豁达的话,包含着多少爱国志士的辛酸与无奈,也映射着执政者的明暗与制度的优劣。 五、有才不得展,有志不得酬,不如出世隐居吧! 《咏史八首》其五: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 有才不得展,有志不得酬,左思想出世隐居了。 六、虽然仕途坎坷、抱负难展,但决不消沉失志! 《咏史八首》其六: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左思虽然没有做过荆轲刺杀秦王那样的壮举,但也与世俗的人不同。左思不把天下四海放在眼里,更别说那些豪门贵族啦。左思不消沉、不失志,仍然自信自豪。
七、英雄也有困顿不得志的时候,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啊! 《咏史八首》其七: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 八、安贫知足,旷达为怀,也不失为一种自我安慰吧! 《咏史八首》其八: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 左思文韬武略,又有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但在不合理的、黑暗腐朽的门阀制度的压抑下,像笼中之鸟,无法冲破束缚,施展抱负。更兼外无俸禄,内无斗储,生活艰难,无人理睬。一个文武兼资的知识分子落到这个地步是多大的悲哀!他对门阀制度的控诉引起了历代读者的同情和共鸣。这是左思的咏史诗受人喜爱和推崇的根本原因。 安贫知足,旷达为怀,也不失为一种自我安慰吧。
佚名
肆/
其五这首诗的前半首写京城洛阳皇宫中的高大建筑和高门大院内的“蔼蔼王侯”。后半首写诗人要摒弃人间的荣华富贵,走向广阔的大自然,隐居高蹈,涤除世俗的尘污。
诗歌的前半首“皓天舒白日”六句,是描绘京城洛阳的风光。诗人登高远眺,呈现在眼前的是:晴朗的天空,耀眼的阳光普照着神州大地。洛阳城皇宫中一排排高矗的建筑,飞檐如同浮云。在高门大院里,居住着许多王侯。这不是单纯的风光描写,它反映了西晋王侯的豪华生活。上一首《咏史·济济京城内》诗的前半首,表面上是写汉代京城长安的王侯,实际上表现的也是西晋王侯的豪华生活。所以,何焯认为“‘济济’首,谓王恺、羊琇之属。”王恺、羊琇都是西晋王朝的外戚,他们生前都过着奢侈的生活。当然,这两首诗的内容不同,《咏史·济济京城内》侧重写王侯的来来往往、寻欢作乐的情景,这一首却是描写王侯的高大住宅。应该指出,这都不是一般的风光景物和人物活动的描写,也不只是表现当时王侯贵族的豪华生活,而是当时门阀统治的象征。正是这些王公贵族掌握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形成了门阀统治,主宰了像左思这些士人穷通的命运。“列宅”二句以鸟瞰笔法写王侯所居,不仅场面宏大,更显得诗人的自居之高。此中含蕴的感情与诗歌结尾相互贯通,表现了诗人追求隐居高蹈,和那些攀龙附凤者不同的志趣。
同时,从这些关于洛阳的描写,读者还可以从侧面看出,左思《咏史八首》当写于洛阳。据《晋书·左芬传》记载,左思的妹妹左芬于公元272年(泰始八年)“拜修仪”,而左思是“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晋书·左思传》)的。结合《咏史》其一来看,可以断言,这组诗是公元272年(泰始八年)以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写于京城洛阳的。
在门阀社会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像左思这样出身寒微的士人,往往壮志难酬,备受压抑。正是仕途的迍邅,使他渐渐醒悟:“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意思是:自己不是攀龙附凤之人,为什么要到洛阳这种地方来呢?其实,左思曾是“攀龙客”,他希望能跟随王侯将相,追求功名利禄,只有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才感到无限的悔恨。于是,他下定决心,与门阀社会作最后的决裂:“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他决心穿着粗布衣服,追随高士许由过隐居高蹈的生活。许由是传说中的隐士。据《高士传》记载,唐尧要将天下让给他,他拒不接受,逃到颍水之滨,箕山之下隐居。左思要像许由那样隐居高蹈,虽然只是一时的排忧解闷之辞,但也是对门阀统治的强烈反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写的是左思所想象的隐居生活。在高山上抖衣,在长河中洗脚,表示他要涤除世俗的尘污。写得豪迈高亢,雄健劲挺。所以沈德潜评曰:“俯视千古。”(《古诗源》卷七)
这是左思《咏史》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它不仅表现了诗人愤懑的感情,同时也表现了诗人高尚的情操,是西晋五言诗的扛鼎之作。
佚名
伍/
其一:此首从“左眄澄江湘”看,应是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年)平吴以前所作。它是《咏史》的总序。一方面叙述自己文学才能的卓异,一方面抒写自己深通兵略,有志于保卫边疆,为国立功,功成身退,不受赏赐。 其二:这首诗反映了曹丕颁行九品中正制之后,所形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平等现象,揭露了这种为巩固士族门阀利益的制度的阶级本质,抒发了自己的愤慨和不平。 其三:这首诗是歌颂段干木和鲁仲连那种有功于国而不受爵禄的高尚节操。作者一则把这两个历史人物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一则是用以批判那些尸位素餐,一心希望厚禄的官僚们。歌颂古人,目的在于讽今。 其四:这首诗是赞扬扬雄穷困著书的生活,而以王侯贵族的荒淫奢侈生活作对比。一半写王侯贵族享尽当世的荣华富贵,死后与草木同腐;一半写扬雄受尽人生的艰苦困难,死后却流芳百世。作者以扬雄自比,也以扬雄。 其五:这首诗是抒发自己和那些攀龙附风者不同的出尘高蹈的思想。其中关于京都宫室的壮丽、侯门的豪华的描写,都是用来反衬自己胸襟的高洁。 其六:这首诗是歌颂荆柯那种睥睨四海、蔑视权贵的精神,说明荆轲虽然刺秦王未成功,但他的行为和那些只贪图爵禄的贵人比,却如千钧和尘埃那样轻重悬殊。歌颂荆轲,借以表示对权贵的蔑视。 其七:这首诗是感叹西汉主父偃等四人的穷困坎坷,进而说明古往今来被埋没的人才很多。是咏史,更是伤今。是由于作者自己被遗弃而发泄愤慨和不平。 其八:这首诗可能是作者有感于魏晋之交,士大夫阶层的修起倏落、乍荣乍枯的境遇,而抒发自己隐逸的情感。贫士生活虽然穷困,但苏秦、李斯那种际遇也不值得羡慕。自处之道应该是安贫乐道,做个旷达之士。
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本站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站将会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E-mail:975644476@qq.com
本文链接:http://chink.83seo.com/news/67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