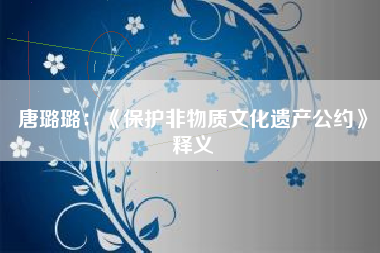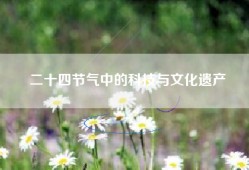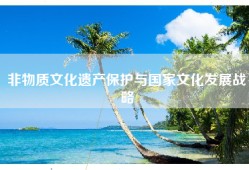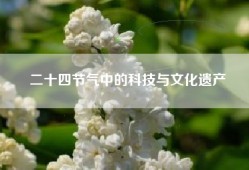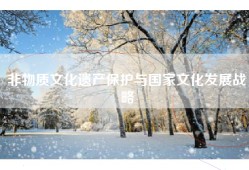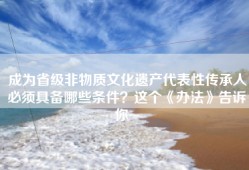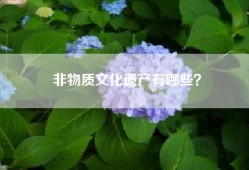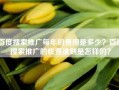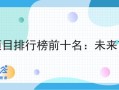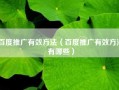唐璐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释义
- 资讯
- 2025-03-04
- 79
【摘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文化遗产领域具有全球影响的重要公约之一。该公约的通过,既有《老鹰之歌》“不眠广场”等关键事件的影响,也有挽救《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失效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缺失的内在需求。该公约形塑了一种全新的遗产保护范式,即赋权社区、群体和个人。缔约国大会和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及其相关文件,保证了该公约的正常实施和各缔约国的履约。
【关键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2003年公约”)于2003年10月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上通过,2006年4月20日正式生效。2003年公约是继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1972年公约”)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领域通过的又一项形塑遗产保护范式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公约。截至目前,2003年公约共有180个缔约国①,在UNESCO的成员国中批准者超过90%,接近全面批约②。
一、2003年公约的缘起
(一)关键事件:从《老鹰之歌》到“不眠广场”
关于2003年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概念的起源,国内外学者已做过详细梳理③。因此,本文不再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细致爬梳,而是关注几次关键事件,或者说是几个故事,它们对于启动2003年公约具有重要影响;其本身也已成为一种民间叙事,是非遗领域相关学者、专家、UNESCO官员等谈起公约源头绕不开的话题。
1.一首歌与一封信
1970年,美国流行音乐唱作人保罗·西蒙(Paul Simon)和阿特·加芬克尔(Art Garfunkel)发行了一张名为《忧愁河上的金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的专辑④。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流行音乐将与文化遗产发生碰撞,并持续几十年影响了关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讨论。该专辑中的一首歌曲《老鹰之歌》(El Condor Pasa)大受欢迎,也获得了众多艺术家的青睐,在随后几十年中不断被改编。然而,这首歌曲引起了巨大争议,既包括对其所有权的跨国争议:秘鲁政府宣布《老鹰之歌》为国家文化遗产,玻利维亚则一直表达这是属于玻利维亚的民歌;也包括歌曲著作权及相关利益归属的争议:是属于创作歌曲的艺术家,注册版权的作曲家,还是安第斯山的土著人⑤?
这些争议,以1973年玻利维亚共和国外交和宗教部部长致UNESCO的一封信达到,这封信被UNESCO视为2003年公约诞生的礼炮⑥。信中声称,当前,民间音乐、舞蹈、手工艺等形式没有得到任何国际公约的保护,正遭受非法、隐秘的商业化和输出,而这些行为是对传统文化的严重破坏。先不论玻利维亚政府保护民间文化的立场问题⑦,这封信的结果就是UNESCO开始更为关注民间文化保护问题。事实上,UNESCO通过1972年公约之后,就有一些成员国关注到保护“非物质遗产”(当时还未形成此概念)的重要性。之后,UNESCO于1982年设立了非物质遗产处(Section for the Non-Physical Heritage)⑧。但这一时期,UNESCO关注的重点或者说保护理念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考虑的,因此,是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推进工作的⑨。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以下简称“1989年建议案”),这标志着在对民间创作的保护上,UNESCO与WIPO分路扬镳⑩。该建议案明确了“民间创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⑪,也就是说,不再强调民间创作是某国、某区域或某人的私有财产,而是为全人类共享的。因此,保护的重点就不是注册知识产权,而是转移到其存续力上⑫。它强调:“各国政府在保护民间创作方面应起决定性作用,并应尽快采取行动。”⑬这种转变,与UNESCO一贯的立场和愿景也是一致的,就是讲求文化的多元化、包容性,要建立对话和相互理解的渠道,消除仇恨与偏狭,从而推进人类和平⑭。
2.一个广场与一次会议
“不眠广场”(Jemaa el-Fna)⑮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麦地那⑯入口处,存在历史已逾千年,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唯一仍在使用的广场。“不眠广场”是摩洛哥乃至整个非洲最繁忙的市场之一,历来是当地各种民间表演的场所:讲故事、耍蛇、算命、吃玻璃、杂耍、音乐和舞蹈表演,等等;晚上,广场则化身大型的露天餐馆,从水果摊到烤肉摊一应俱全,吸引着摩洛哥和国外的游客。然而,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社会和文化功能的空间却面临现代化的侵蚀。20世纪90年代,马拉喀什市政当局和一些商人计划拆除广场周围的几座建筑,代之以一座高层购物中心和为购物者服务的地下停车场⑰。
以长期居住在马拉喀什的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为代表的一批民间人士开始为保护这个“不眠广场”奔走。他们成立了非政府组织“广场之友”(Les Amis de la Place)并向UNESCO寻求帮助⑱。1996年,戈伊蒂索洛联系了时任UNESCO总干事的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希望UNESCO通过授予荣誉的形式,给予“不眠广场”国际认可,从而保护该文化空间。戈伊蒂索洛与马约尔见面时,进一步提出了保护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及人类创造力的重要性⑲。马约尔非常支持戈伊蒂索洛的建议,而且恰逢UNESCO在筹备非遗公约(即后来的2003年公约)的相关工作,因此这一呼吁得到及时响应。1997年,在总干事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UNESCO在马拉喀什召开了一次关于保护大众文化空间的国际研讨会⑳,除了聚焦“不眠广场”的价值与困境,也旨在推进非遗保护的国际行动㉑。马拉喀什会议从推土机的铁臂下抢救了“不眠广场”㉒;也推动了“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㉓计划的协商,成为助力2003年公约通过的加速器。
(二)现行文件的失效与缺失:1989年建议案与1972年公约
如果说《老鹰之歌》和“不眠广场”在推动2003年公约的通过方面有偶然的因素,当时国际文书在非遗保护方面的缺失则是促使UNESCO通过2003年公约的内在动力。
1.1989年建议案的失效
2000年前后,民俗学领域盛行(自我)批评风潮,这也间接影响到对1989年建议案的评估与反思。经过十年的发展,人们发现,由民俗学者和政府官员精心编制的1989年建议案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因此,数名民俗学家、人类学家、遗产政策决策者等以及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民俗与文化遗产中心,于1999年在美国华盛顿联合召开了一次会议,试图挽救该建议案的失败㉔。与会人员提出,在遗产政策和项目保护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缺失的,因此,为了有更好的依据以及更有效的政府行动,“建议增加对那些跟创造、保护、研究及传承民俗和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群体的列举和说明”㉕。这就明确了利益相关者参与非遗活动的重要性。
此次华盛顿会议对1989年建议案的评估,为2003年公约提出新的遗产保护范式提供了重要经验,包括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与可持续发展结合,突出文化经纪人的重要性等方面㉖。
2.对1972年公约的批评
UNESCO通过1972年公约的背景是: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保护历史遗迹的运动;另一方面,面对前所未有的环境恶化和物种灭绝,环保主义开始盛行。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与自然遗产保护相结合的理念应运而生。1972年公约为很多相关的国际救援行动提供了制度框架㉗。
尽管1972年公约在全球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它也在很多方面招致批评。例如,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主要是欧洲的、教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都偏少;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失衡,名录的遗产项目主要集中在欧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项目数量极少。除此之外,1972年公约受到的严肃批评主要包括四点:一是碑铭主义(monumentali),该公约对于文化遗产的定义根源于欧洲的历史建筑概念,对规模和特权过于迷恋,遗产名录更关注宫殿、城堡、大教堂等形式。二是物质主义(materiali),与碑铭主义紧密相关,该公约将遗产限定为“有形”的,从而制造了遗产的二分概念㉘,并且强调了物质的重要性。三是生态隔离(ecological apartheid),虽然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被置于同一个框架下,但也彻底区分了对自然和文化的保护,若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话,二者是有不同衡量标准的。这种自然与文化二分法,将人类生活从自然环境中彻底剥离了。四是真实性原则(doctrine of authenticity),这也是近年被人们一直反思和重新评估的。现在对真实性概念的普遍看法是,这是极其欧洲中心主义的,将影响《世界遗产名录》在全球的信誉㉙。
正是因为1989年建议案在实践中的失效和1972年公约被诸多诟病,一份更具操作性,更能体现UNESCO对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题态度的国际性文书呼之欲出。
二、2003年公约中的重要概念与理念
(一)非遗的概念及特征
2003年公约的宗旨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㉚。究竟何谓非遗?根据2003年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遗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㉛。
非遗有两个重要特性。首先,它是具有包容性的,人们“可以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可能与其他人的实践相似”,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引发特定的实践是否专属于某种文化的问题”㉜。因此,在2003年公约框架下,不鼓励用类似“独特的”(unique)这样的形容词描述非遗项目。其次,非遗具有活态性,是在不断变化和演进的,保护的目的是确保其存续力,“保护的重点在于世代传承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过程(processes),而非具体表现形态的产物(production)”㉝。包容性与UNESCO主张文化多元化的一贯立场一致,也是与现有国际人权文件一致的,符合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互相尊重的需求;而活态性则体现出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赋权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遗产保护范式
如果说1972年公约的遗产保护范式是由专家和政府主导的,2003年公约所采取的则是一种全新的赋权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遗产保护范式,这也是吸取了1989年建议案的经验教训,吸纳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遗产活动。2003年公约第十五条奠定了这种遗产保护范式的基础:“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㉞
需要说明的是,2003年公约对于“社区”“群体”和“个人”没有明确定义,所有尝试定义这些概念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社区”“群体”和“个人”在2003年公约框架中是一种敏化性(sensitizing)概念,而不是确定性(definitive)概念㉟。任何说明或者限定,都会削弱2003年公约范式的影响力、可能性和适用性㊱。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是作为一整条准则出现在2003年公约的基本文件中的,也即“社区”“群体”“个人”是享有平等地位的。但在非遗保护实践中,甚至是在UNESCO系统内部,都存在一种偏向,就是赋予“社区”一词特权,对其提及和强调远多于“群体”和“个人”㊲。这种倾向可能是为了减少这一套敏化性概念带来的复杂性,但同样会削弱2003年公约范式的适用性,因此是要避免的。只有保持“社区”“群体”“个人”的平等地位,才能保证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非遗活动中,从而保证这种新的遗产保护范式的有效性。
三、2003年公约的运行机制
2003年公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缔约国大会,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常会;同时,在UNESCO内设立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委员会委员国由缔约国大会选出,任期四年,按规则进行换届。
缔约国大会与委员会会议定期召开,保证了2003年公约也具有“活态性”,与该公约相关的“工具包”能随着非遗全球实践的发展及时更新。例如,2015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常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该等伦理原则是对2003年公约、实施该公约业务指南和各国立法框架的补充,旨在作为制定适合当地和部门情况的具体伦理准则和工具的基础。”㊳2018年6月,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第七届会议上批准了总体成果框架。“总体成果框架含有清晰确定的目标、指标和基准以及以成果为导向的监测系统,是衡量2003年公约对各级影响的工具。”㊴该框架确定了非遗保护的长期、中期、短期成果以及8个专题领域;在8个专题领域之下,确定了一组26项核心指标以及一组86项相关评估要素,旨在有效评估2003年公约的产出、成果和影响。
各缔约国在实施2003年公约时,主要遵循《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根据非遗全球实践,《业务指南》也会及时由缔约国大会修正。例如,为了将2003年公约与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结合,《业务指南》新增了第六章“在国家层面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从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容性经济发展、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非物质遗产与和平这四个主要方面明确了保护非遗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
2003年公约在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一项工作是委员会根据缔约国的提名,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优秀实践名册》,这也是在国际一级保护非遗的重要措施。《业务指南》对相关列入标准有详细说明。在2003年公约生效前被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项目全部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根据《业务指南》第二十七条,委员会设立的名为“审查机构”的咨询机构负责对相关名录的申报、推荐以及10万美元以上的国际援助申请进行审查。审查机构负责向委员会提出建议,以便其做出决定。委员会在公平考虑地域、非遗各领域的代表性后,确定12名审查机构成员,包括来自非委员会委员缔约国的6名非遗领域合格专家和6个经认证的非政府组织㊵。根据1972年公约,主要由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罗马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以及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等专业机构为其委员会提供咨询㊶。而根据2003年公约第九条:“委员会应建议大会认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确有专长的非政府组织具有向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的能力。”㊷目前,全球共有193个经缔约国大会认证的非政府组织向委员会提供咨询㊸,未来还将继续增加。可以发现,与1972年公约相比,2003年公约委员会在进行决策时,除了向专家或专业机构咨询,也非常重视非遗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建议。咨询机构数量多,覆盖非遗各个领域,也考虑到地域平衡,可以及时吸收到来自全球非遗实践的反馈,吸纳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非遗保护的活动中,这也是符合2003年公约一贯立场的。
同时,2003年公约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根据UNESCO内部监督办公室(Internal Oversight Service)在2013年对使用该公约的第一个十年进行评估的结果,可以发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于履约存在一系列误解。例如,将2003年公约与1972年公约的概念和原则混淆;社区对自己的非遗项目缺乏认识等㊹。因此,2003年公约期望通过赋权社区、群体和个人而建立的“自下而上”的遗产保护范式,距离真正实现仍要跨越现实的鸿沟。在该公约实施中,需要克服面临的全球性、地区性和全球在地化的问题;而缔约国也需要在非遗保护实践中不断思考国际规则与地方实践的缝合,以推进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欧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及重要案例研究”(项目编号:17CH2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注释:
① 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003) [EB/OL]. [2021-05-01].
②㉚㉛㉞㊳㊴㊵㊶㊷ UNESCO. 基本文件: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2021-05-01].
③相关研究参见:Noriko Aikawa. An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04 (56);巴莫曲布嫫.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J]. 民族艺术,2008(1):6-17. UNESCO将与2003年公约通过相关的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46年至1981年的第一阶段;1982年至2000年从世界文化政策大会到发布《我们创造性的多样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报告;2000年以后及公约起草阶段。参见:Working towards a Convention[EB/OL]. [2021-05-01]. https://ich.unesco.org/en/working-towards-a-convention-00004.
④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 & Garfunkel)二人组合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民谣组合,该专辑是两人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获得了当年的格莱美唱片奖,也是该组合销量最大的专辑。
⑤⑥沃尔迪玛·哈福斯坦,张举文. 山鹰之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造过程[J]. 文化遗产,2018(5):79-83,79.该文为哈福斯坦专著的一个章节,也可参见其专著:Valdimar Tr. Hafstein. Making Intangible Heritage: El Condor Pasa and Other Stories from UNESCO[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⑦当时的玻利维亚政府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事专政政府,而写信的外交和宗教部部长是一名主义者。土著人艾马拉人和克丘亚人的身份实际上正受到强力压制,他们被要求认同为玻利维亚同胞,他们的歌曲和舞蹈被政府挪用为玻利维亚的国家文化。参见:沃尔迪玛·哈福斯坦,张举文.山鹰之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造过程[J]. 文化遗产,2018(5):82.
⑧巴莫曲布嫫.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J]. 民族艺术,2008(1):6.
⑨⑩施爱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内在矛盾[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1):5,6.
⑪⑬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EB/OL]. [2021-11-24].
⑫详细的学术史梳理可参见:施爱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内在矛盾[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1):2-11;朱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件史考述——基于《建议案》和《“代表作”计划》的双线回溯[J]. 青海社会科学,2019(6):214-219,238.
⑭UNESCO in brief-Mission and Mandate [EB/OL]. [2021-05-01]. https://en.unesco.org/about-us/introducing-unesco.
⑮也有音译为“杰马夫纳广场”“德吉马广场”,本文采用国家更为熟知和通用的“不眠广场”。
⑯即旧城,1985年“马拉喀什的人聚居区”被列入UNESCO《世界遗产名录》。
⑰⑱㉑㉗㉙Valdimar Tr. Hafstein.Making Intangible Heritage: El Condor Pasa and Other Stories from UNESCO[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8:91-92, 93, 93, 58, 59-62.
⑲朱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史考释——基于从马拉喀什会议到《“代表作”计划》的演进线索[J]. 民俗研究,2020(5):9.
⑳关于马拉喀什会议详细的学术史梳理,可参见:朱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史考释——基于从马拉喀什会议到《“代表作”计划》的演进线索[J]. 民俗研究,2020(5):9.
㉒马拉喀什市政当局此后为“不眠广场”制订了详尽的保护措施,但“保护”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可参见:Valdimar Tr. Hafstein. Making Intangible Heritage: El Condor Pasa and Other Stories from UNESCO[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8:98-101.
㉓“代表作”一词原对译的英文单词Masterpiece背后的逻辑意味着遗产有等级之分,后来被更显公平的Representative list替代。
㉔㉕㉖㊱㊲马克·雅各布,唐璐璐. 不能孤立存在的社区——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防冻剂的“CGIs”与“遗产社区”[J]. 西北民族研究,2018(2):12-23.
㉘即使后来通过了2003年公约,在UNESCO的框架下,遗产仍然是被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这种二元对立依然存在。
㉜㉝巴莫曲布嫫. 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J].民间文化论坛,2020(1):115,117.
㉟确定性概念是“事务的概念”,而敏化性概念是“关系的概念”,前者适用于自然科学中的独白式论题,而后者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对话式论题。敏化性概念没有明确的属性和参照点,但在处理经验实例时可以提供参考感和方向感。参见:刘力,管健,孙思玉. 敏化性概念、基耦与共享:社会表征的对话主义立场[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10(1):217-233.
㊸Accredit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advisory services to the Committee [EB/OL]. [2021-05-01].
㊹Barbara Torggler, Ekaterina Sediakina‐Rivière. Evaluation of UNESCO's Standard-setting Work of the Culture Sector: Part I-2003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INAL REPORT [EB/OL]. 2013:39-40 [2021-05-01]. https://ich.unesco.org/doc/src/IOS-EVS-PI-129_REV.-EN.pdf.
▼ 作者简介:
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本站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站将会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E-mail:975644476@qq.com
本文链接:http://chink.83seo.com/news/71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