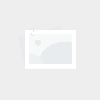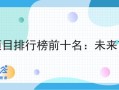万方:艺术创作需要真实的表达
- 资讯
- 2024-12-16
- 68
来源:财新视听一线人物
嘉宾:作家剧作家万方
主持:毕啸南
万方与毕啸南
作家、剧作家万方
万方,1952年出生于北京,16岁去东北插队,开始尝试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初,万方以小说《杀人》引起文坛瞩目,随后进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她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空镜子》轰动一时,万方也由此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身为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女儿,万方长久以来没有涉足话剧创作,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源自她对父亲剧作的高山仰止,另一部分也源于万方自己对戏剧创作的敬畏。直到54岁时,由万方任编剧的第一部话剧《有一种毒药》才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尔后,她佳作频出,《冬之旅》《报警者》《新原野》都受到了普遍好评。
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万方对自己笔下女性命运的起伏跌宕感同身受,对生命和情感万方有着更为深刻的见解。在《女人心事》的序言中,万方写道:“女人一生最黑暗和最耀眼的,都是婚姻和爱情。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这是万方长久以来的思索,也是父亲曹禺的三段婚姻生活带给她的启示。
身为从小接受家庭熏陶的文艺创作者,万方深切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但她相信艺术创作的原理并未改变,恐怕也不需要改变。
万方:灵魂需要真实表达
01
父亲给我压力也给我动力
毕啸南:您怎么看待曹禺的女儿这个身份?
万方:曹禺女儿这个身份确实经常会被人提到,尤其是前些年我写的电视剧《空镜子》播出的时候,采访或者是朋友间(说起)都会说“这是曹禺的女儿”。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曹禺的女儿,我觉得有压力吗?我很本能地回答说没有。父亲就是父亲,作为女儿,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了不得的人,著名的剧作家,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像朋友一样和孩子相处的爸爸。2006年,我的第一部话剧《有一种毒药》在首都剧场演出。因为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那天去剧场的路上,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我的戏要在首都剧场演出了。”这时候我忽然心里一动,我想,看来作为曹禺的女儿,这么多年来我其实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他的那几部作品,一直压在我头上,让我不敢写戏,不敢写话剧。就是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也许达不到他的高度。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作为曹禺的女儿,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从他身上遗传了一种性情,或者说是素质,就是敏感。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敏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素质。因为你要写人,你要塑造人物,你就需要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本领。当然,同时你还要能跳出来,否则也没法写了。
毕啸南:从你的角度来讲,曹禺是什么样的人?
万方:爸爸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用一句话说,我觉得他就是一团感情。他是一个感性动物,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周围的一切、对于他自己的经历,他都以感情来面对。他不是一个战士。他有思想,但他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写作的人。
我觉得他的性格其实是比较懦弱的。他很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样子,那时候我爷爷在通化当镇守使,军营里经常有军号声,听到后他会非常难过,甚至流泪。我爷爷就问他,你这么小的孩子,哪来那么多哀伤?我想这是他的一种天性。我说他懦弱是指,面对痛苦的事情,有的人会睁大眼睛迎上去,而我父亲,他面对痛苦的时候,会低下头、闭上眼睛。他不是那种遇到不公正的事情会站出来争辩、抗争的人。我觉得他的勇敢都在他的作品里了,他把一切情感都倾注在自己的作品里,他是用作品说话的人。
如果说他的性格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真诚。如果允许自由表达,我觉得他的喜怒哀乐一分钟都不会多停留在心里,都会立刻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喷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悲剧。他在23岁就写出了《雷雨》,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都是经典,但太少了,应该有更多的,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遗憾。
他这一代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都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苦难,很多人都和他一样,像沈从文,后来也改行去研究古代服饰了。你说后来他心里有没有话想说?我想肯定有。但如果不能真实地表达,我觉得他可能就觉得那干脆就不表达,或者说也不会表达了。
这一点我今天也有同样的体会,作为一个精神领域的创作者,在我需要创造力的时候,如果不能够自由地表达,可能我就要失去创作的能力。
毕啸南:说到家庭,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家庭单元,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万方: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在家庭环境中才是最真实的自己。每个人在社会上,可能会戴上面具,可能会扮演角色,但不可能永远戴着一个假面具。而在家庭里,配偶或者子女是你最亲密的人,要维持最长时间的关系,所以会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反过来说,每一个人在家庭中所获得的或者受到的影响,应该说是最大的。
我父亲那一代人,他(们)的家庭有一种压抑苦闷的气氛,我小时候也类似。正是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我们学校附近北京人艺的一个仓库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我们家的门上也贴满了打倒我父亲的大字报。有人会到家里来抄家,把柜子贴满封条,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痛苦的回忆。但是我后来经常会想,痛苦对于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思索(痛苦)会让人更有智慧。
毕啸南:是不是因为当人快乐的时候,他不会去想,因为反正快乐。但是他痛苦的时候,就一定要找到它的原因?
万方:对。人为什么痛苦?痛苦从哪里来?这些问题会让人改变自己,或者改变使他痛苦的环境,于是人就有了追求,有了奋斗的力量。所以痛苦的记忆,我觉得不完全是坏事,甚至更放大一些,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也不见得完全是坏事情。
毕啸南:这是一个批判性的肯定。
万方:是。其实我的《冬之旅》写的就是我们要不要忏悔,我们要不要宽恕,我们能不能忏悔,我们能不能宽恕。
毕啸南:除了时代环境的变化,你和曹禺最大的差异性在哪里?比如说性别的差异,创作视角的差异,语言风格的差异,你有没有做过一些比较?
万方:我们的创作视角确实不同。人们经常会问我,作为一个女性,你的写作是不是更关注女性?我想这是一种自然,因为对每一个人来说,性别都是一个很重大的差异—让你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不一样—但我也有一个意识,就是不要被我的性别所束缚。
毕啸南:你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
万方:应该是我的小说《杀人》,那是我写作的一个转折。我的那篇小说写的是一对农村婆媳,虽然我在农村插过两年队,但还是离我自己的生活比较远,写起来很困难,越写越灰心。
万方中篇《杀人》首发于1994-3《收获》
爸爸曾经说过创作要眼高手低。一般来说这是个贬义词,但他说写作的人就是要眼高手低,因为你不可能一上来手就很高,但你应该眼高,眼高就是知道什么是好的,你要达到什么水平,往哪儿走。那时候我知道我虽然手低,但是眼还可以。我看着自己写出来的一段一段,心想我要是只能写成这样,那真没什么意思。然后有一天忽然写出了一段,一下让我眼睛一亮。我心想这感觉对了,就从那一刻往后,我觉得我上了一级台阶。
毕啸南:这种创作上的顿悟,有理由吗?
万方:没。你想不出理由。它实际上是一种积累,忽然从量变到质变。那个小说写出来之后,被《收获》发表了。那时候我爸住在医院里,我就把那一期刊物留给他看。第二天他一见我进门,眼睛就亮了,就叫我:“小方子,你快来。”我走过去,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你写的小说我看了,你真行,你真能写。”这件事我现在想起来都特别高兴,那时候我觉得我能吃写作这碗饭了。
毕啸南:戏剧是什么?戏剧的力量在哪里?
万方:如果让我排序,我觉得诗人是最高的,诗人是上帝的手点到你头上,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了;第二是戏剧,因为它是在限制中做文章,有时间的限制,有空间的限制,所以它更难;第三是小说和影视,当然电影也有很棒的;电视则更多的是一个娱乐产品。在今天,实际上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里,戏剧的观众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但即便如此,戏剧还是小众的,跟动不动票房就几亿的电影是没法比的。
但我恰恰认为这种小众是戏剧的优势,因为艺术最重要的特性就是个体表达。前些天有一部话剧《4:48精神崩溃》,是一个英国女剧作家写的。她写的是精神崩溃的过程,那是非常极致的一种感受,但是我认为这种个体的感受代表了所有人,因为人类就是由每一个个体所构成的。戏剧不像电影,因为是人现场表演,顶多一天两场,所以它的受众有限。但它可以和这一部分人进行独特的、更个人的沟通。
戏剧的意义应该是尽可能生动、深刻地展现人性,描摹我们生存的困境。至于有没有答案,我觉得这要交给观众。
但是现在也确实面临着一个情况,就是缺乏好的剧本。这可能是因为戏剧总体来说不大赚钱,特别是严肃戏剧,你如果想靠它来赚钱,那是不可能的。但人都想生活得更好一点儿,获得更多的物质,我曾经写过影视剧,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总的来说,人还是要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这样的人是最幸福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大家先去挣钱,先吃饱饭,再回来创造。
如果说年轻人想要走这条路,那就需要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大红大紫不会那么容易、那么快。再有,戏剧是很吃功夫的—尤其(是)作为编剧,所以要不断(地)学习。首先是可以看好的作品和演出;再有就是向生活学习,学会体验和体味人生,自己和别人的人生。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好编剧。
02
的年代
毕啸南:你父亲和巴金是好朋友吧?
万方:巴金本名叫李芾甘,所以我都叫他李伯伯。爸爸跟他是一生的朋友。当年他(指曹禺)的《雷雨》写完之后,把剧本给了他在南开中学和巴金一起办《文学季刊》的好朋友。这位朋友可能是忘记了,直到一年后巴金在抽屉里看到《雷雨》的剧本,读后感动得泪流满面,并决定立刻发表出来。后来《收获》发过一篇他们两个老人各自在医院的通信,我读了很感动。我记得作家方方当时还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她读了那些信非常感动,说那就是友谊的样子。
我爸住院赶上过节,正好那时候巴金也在住院,两个人就各自在医院的电话间里通话。结果两个人还都听不清,在电话间里大嚷:“我要去看你!你什么时候来?”
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的生命,是很有分量的,今天的人变轻了,包括我自己。这背后的原因很多。社会在变,包括互联网带来的巨大便利,令我们的生活变得那么方便,甚至过于方便。但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思念,我们现在很少像以前的人那样去思念另一个人了。而这种思念实际上缔造了很多伟大的作品,尤其是一些诗歌,都是从这种思念中生发出来的。
毕啸南:为什么你父亲那个时代会涌现出许多级的人物?
万方:我爷爷是一个军阀,而且是一个大烟鬼,我父亲的哥哥也抽大烟。《北京人》里边有一段父亲给儿子下跪,求他别再抽大烟(的情节),原型其实就是我爷爷给他儿子下跪,他自己抽没事儿,但是儿子抽他受不了。爸爸从幼年到少年,一直就在这种很压抑的环境中长大,非常寂寞,然后他希望能亲手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都有这样的希望,都怀着这个希望,尽每个人不同的努力,对爸爸来说就是写作。而且他可以自由地表达—当然也不是绝对自由,《日出》当时也被禁演过,也来抄过家,但毕竟让他写出来了。我觉得民国时期是混乱的,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都在自己的空间里施展拳脚。这种混乱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机。
毕啸南:你说的是自由对于知识分子的意义。这种自由的关键在于多元,就是要允许不同的内容共生。所以会有人说,宽容是自由的前提。不过有些时候,人们会把多元化的状况理解为一种无序,就是你说的混乱—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在负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社会学的研究早已证实,复杂社会才能涌现创新,如果是人为制作出来的,怎么能叫创新呢?水至清则无鱼,道理简单,关键看你怎么看,你是要一池清水,还是想要鱼?
万方:自由对于所有的人都是最重要的。我不能设想我是没有自由的。当然这个“自由”是相对的,一种是身体的“自由”,一种是心灵的“自由”。心灵的“自由”特别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他(的)思想和创造力的前提。
03
爱情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情感
毕啸南: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万方:我想写我的爸爸和妈妈。实际上想了很多年,但是我一直不能写。因为我父亲有三段婚姻,(与)我母亲(的婚姻)是他的第二段。他跟我母亲相爱的时候,实际上他还在第一段婚姻之中,所以对我来说,过去一直有一种很难描述的心理障碍。
我需要把自己真正说通,这样我就能写了。我觉得(我)正在慢慢地跟自己握手。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非常开放的,关于婚姻、爱情或者是两性关系,但是一旦涉及自己,(我)还是没有办法。这让我意识到我还是一个中国女人,被一些东西束缚住,这个我真是没想到。
毕啸南: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只要发乎于真情,就是美好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万方:你这个问题很复杂,这甚至牵扯我们为什么要活着。看起来我们活着有很多意义,要承担责任,要享受生活,要爱,要被爱,要生孩子……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自己。就说婚姻吧,当两个人已经没有爱,对于像我父亲这样敏感的人,可能婚姻就会成为一个枷锁,维持下去是一种痛苦。
毕啸南:对方也痛苦。
万方:是的,对方也不会愉快,也不会幸福。不光是我父亲,很多人,包括鲁迅,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做好自己,真诚地对待自己。说到伤害,什么是伤害呢?我觉得这个词不要跟道德绑在一起。
爸爸的三段婚姻都是真爱。第一段婚姻结束我觉得是因为性格不合,其实结婚前他的朋友,包括吴祖光等人,都在劝他。可他还是要结这个婚,因为他觉得他有责任,但是最终还是分开了。
第二段婚姻是他跟妈妈,我觉得他是一见钟情。到“文化大革命”,因为爸爸被“打倒”,我慢慢意识到,妈妈因此变得很痛苦和绝望。后来我读到了当年爸爸写给妈妈的信,信纸写得密密麻麻,像是爬满了小蚂蚁。看了这些信,我特别为妈妈觉得幸福,因为她这一辈子享受到了那样的爱情。
妈妈是1974年去世的,爸爸的第三段婚姻是6年以后了。我的继母——我也叫她妈妈——我觉得他们俩的婚姻也非常好,他们俩真的是无话不谈,虽然我不知道他们都谈些什么。他们对彼此的坦诚,在夫妻间非常难得。
我从爸爸的这三段婚姻里得出了一个感受,就是爱情这个东西,不管它多长,不管它多短,确实是人一生中所能经历的最好的情感。能够经历和感受爱情的人是很幸运的。
毕啸南:你个人呢?
万方:我当然也尝到了。
毕啸南:我觉得最后这句特别完美。
04
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因为不自由而失败
在说我和万方老师的渊源前,我先说说另一位女性作家—方方。2017年5月,我经朋友介绍,约了方方老师做《女性领袖人物》专访嘉宾。6月,在天津大剧院,钱程院长约方方老师北上看纪念史铁生的戏,方方老师考虑我节目录制方便,也是替我省钱,特意打电话来告知,说如有需要可以来趟北京。后来因故未能成行,我心中依然非常感谢。回想起亚妮也是如此,自己掏腰包买机票来北京录的节目,早上来下午回,特此一表。
方方——万方,名字就差一个字,这真有趣、有缘分。作为戏剧的女儿,万方的成长之路并不平凡,说不平凡,既有名门之后带来的虚名,也有日积月累、耳濡目染的真才实学,更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目睹的残酷与荒唐……这些话题,专访的时候都录到了,虽然没有在节目里播放,但记录下来总有一天会有人想要了解,需要使用。
我和万方老师结缘很早,2012年还在传媒大学念博士时,歪打正着因为一部话剧获得了金狮奖,便被安排和童道明、万方、徐峥、小陶虹、靳东等人一起走红毯,算是初次认识。时隔七年之后,我在央华文化公司王可然的引荐下和万方老师一起做节目,最初我以为万方会是那种“又红又专”的老艺术家,可万万没想到,万方的真实表达,她思想的自由度,都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
“真实”——这两个字难吗?岂止是难!
穷尽这一生,一个人能做的无非是尽力让自己变得真实。而知识分子的真实则更难,因为知识有时候会成为矫饰的花环。所以当万方谈曹禺的懦弱与真诚,谈她对婚姻情感的态度,谈她父母的婚外情,谈“文化大革命”,谈艺术的本质,谈真实与自由……这些说出来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背后却需要讲述人极大的智慧和勇气。这期节目的标题“灵魂需要真实表达”,也是在反复斟酌后确定下来的,我希望能够借此呼唤一些东西。
相比其他嘉宾,万方老师的专访稍显沉重。万方谈及她父亲曹禺及那一代知识分子时表示,那一代文化人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境遇或者说共同的困境、共同的苦难,很多人都和曹禺是一样的——包括他的同学钱锺书——改变了自己的选择。曹禺的心里肯定还有话想说,但是他能说多少,该怎样说?尤其是对于剧作家曹禺来说,真实的表达和表达的真实是两个他必须考虑的问题,更关系到他的创作能力。一个人可以戴着面具面对邻居,但是却很难戴着面具面对镜子。
万方老师对于苦难的理解,以及对于真实的、美好的人性的追求,让我记忆深刻。父亲曹禺被打倒时,万方学校附近的人民艺术剧院仓库和她自家门前贴满了批判曹禺的大字报,还有前来抄家的人,在屋里贴满封条,这些都是她痛苦的回忆。
这些痛苦对于一个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万方给出了她的答案:痛苦让你思索。如果一个人快乐,那么他不需要去思考为什么我这么快乐,他的主要精力会用在享受这份快乐上。但是当一个人痛苦时,他一定要找出痛苦的原因,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防止痛苦再次袭来。至少他会问,为什么我会感到痛苦?痛苦从哪里来?以此为新的出发点,人就会尝试改变造成他痛苦的环境,或者选择逃离当下的环境,去一个新的地方。
所以万方说,回头来看,她个人的经历并非全是坏事。甚至放大一些,痛苦的经历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也不尽然是坏事,关键是如何面对痛苦的记忆,如何选择下一步的行动。
我记得特别清楚,录制完节目我送万方老师下楼,正好是傍晚五六点的样子,盛夏的北京到了晚上还很温暖,斜阳穿过几株柳树的间隙,斑驳地落在我和万方老师身上,我们轻轻拥抱告别,万方老师忽然说:“跟你聊聊,心里觉得宽慰了许多。”
不知道万方老师是否还记得当天她留给我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一位年轻知识分子心上的一份承担。
我想,万方对自由表达的执着,不仅对她这样的作家有意义,而且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一剂良药。用心的读者或许已经感觉到,这期专访有一个潜在的主题,那就是生活与自由的关系。艺术创作需要自由表达,而自由表达需要创作者对生活有充分的体验,同时也需要创作者享有充分表达的权利,这是最直白的逻辑。
借由电视节目《见字如面》,很多人读到了《黄永玉写给曹禺的一封信》,信中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阐述、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如果我们在这里忽略这段话的时间背景,把心中的“戏”替换成“生活”,它是否依然成立?
在我看来,这段话依然成立——生活可以因为丧失自由而变得失败。如果生活为“势位所误”,它就会“从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我们的生活一旦遭到挟持,就会被束缚,失去宽广的可能性,而所谓的精彩人生也就无从谈起。
但是这份自由需要我们每个人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换来。
自由需要丰富和多元作为前提条件。如果生活的可能性被他人或者自己进行了限制,自由便无从谈起。抛开外部因素不说,想做到不给自己的人生划定范围、预设答案,需要的不仅仅是想象力,更要有充分的智慧和扎实的努力。
越是成长,越是和更多不同的人接触,我就越发觉,这个世界之大,人生的选择之多,远远超出我原本的想象,就好像一个人从小到大如果从来没有见过金色,你怎么可能让他去想象丰收的麦田和灿烂的夕阳?比如万方这样的剧作家,如果不去走进别人的生命,不去体会他人的悲苦,她绝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超越性的写作,问题不在于作家创作的想象力是否足够,而是想象力的发展也需要土壤。
中国人喜欢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都是扩展自己生命体验的途径。生命想要获得自由,就需要我们创造一个能够容纳自由表演和展示的舞台。这个舞台既需要国家、社会的搭建,同样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灵魂和头脑的尺度的体现。
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本站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站将会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E-mail:975644476@qq.com
本文链接:http://chink.83seo.com/news/11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