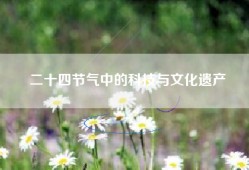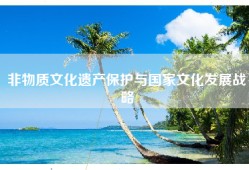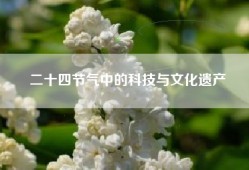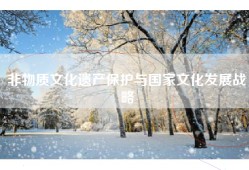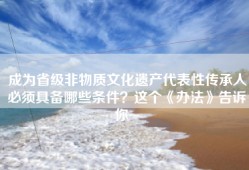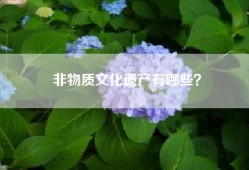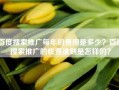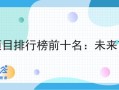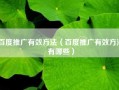刘 鑫:从公开活用走向促进地区振兴:日本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利用
- 资讯
- 2025-03-08
- 66
从公开活用走向促进地区振兴:
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
摘要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国家,在近七十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国家层面,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的总体战略,从最初的公开活用演变到目前强调促进地区振兴,利用程度逐步加深。在地方层面,根据项目差异,对表演艺术、传统技艺、风俗习惯三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各具特点的利用策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管理,依靠多部门、多主体共同推进,并且其趋势为文化遗产的一体化综合利用。这些经验对中国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以及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文化财;“非遗”利用;国外“非遗”
文章编号:1003-2568(2018)05-0088-09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作 者:刘鑫,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随着中国文化消费的快速增长以及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在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基础上,对其合理利用正从最初的忽视逐步发展到认同和重视。目前,个人、社会和政府都在广泛地思考和实践如何有效利用和开发非遗,更好地实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由于中国对“非遗”资源的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出现了“非遗”利用或是效益低下,或是盲目规模化生产、影响核心技艺传承等问题。日本对“非遗”的保护与利用走在世界前列,对“非遗”的利用称作“活用”,它是指发挥遗产的社会功能,通过更多人的欣赏和体验,成为地区和社会的核心力量。早在1950 年,日本就制定了《文化财保》(文化遗产在日本被称作“文化财”),把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纳入法定的保护与利用框架。2015 年,日本实施《文化财综合活用战略计划》,全面推进包括“非遗”在内的文化遗产的综合利用。日本在近七十年的“非遗”利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中国目前推进“非遗”的合理利用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将首先在国家层面分析日本非遗利用的总体战略演变,其次通过三个典型案例,探讨目前在地方层面日本推进“非遗”利用的具体实践策略,最后总结日本经验对中国合理利用“非遗”的启示。
一、日本“非遗”利用的战略演变
目前,日本文化厅把文化遗产的“活用”分为两类:一是公开活用,指以鉴赏文化遗产、公开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介绍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二是促进地区振兴等方面的活用,包括推动地区振兴、旅游业发展、城市建设、教育等,其立足于当前经济社会形势和地区现状,给文化遗产附加上时代的意义和功能,是更为积极的活用。从 1950年《文化财保》颁布开始,日本对“非遗”利用的意识不断增强,利用的总体战略逐步升级,从最初的公开活用扩展到目前强调促进地区振兴等方面的活用。
(一)《文化财保》明确公开活用的重要性
日本对“非遗”利用的政策始于《文化财保》。该保最初把“无形文化财”纳入指定保护范围,包含“艺能”(包括古典戏剧和音乐)和“工艺技术”两类,1975 年又把“无形民俗文化财”(包括风俗习惯、民俗艺能、民俗技术三类,与“无形文化财”区别在于没有特定的传承者,由整个地方社区进行传承)和“文化财保存技术”纳入指定体系,由此形成“非遗”的指定框架。从内容上看,这些“非遗”涉及三种类别:表演艺术(艺能、民俗艺能)、传统技艺(工艺技术、民俗技术、文化财保存技术)、风俗习惯。
这部保不仅强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也指出利用遗产的重要性。该保第一条规定:“制定本法律的目的是保存文化财,并致力于其活用,促进民众的文化进步,从而为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这里的“活用”主要指公开活用,此后的实践也偏重于对“非遗”的保护,弱化了对遗产的利用。例如,在民俗艺能方面,从1950 年开始每年在东京的日本青年馆举行“全国民俗艺能大会”;1959 年开始每年举办五个区域性的民俗艺能大会,大会中的民俗艺能展演被要求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并且减少舞台技术的使用,其目的是提高民众对民俗艺能价值的认识。在艺能方面,1966 年日本《国立剧场法》颁布,同年 11月日本国立剧场在东京千代田区建成运营,此后日本的国立演艺场、国立能乐堂、国立文乐剧场等国立传统艺能剧场在不同地点建成,其主要目的是举行传统艺能演出、培训继承者以及研究和振兴日本传统艺能。
(二)技艺类“非遗”最先被加大利用力度
1974 年颁布的《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以下简称《传产法》)推进了传统技艺类“非遗”资源的利用。从本质上讲,技艺是通过生产(或者生活)进行传承,因此,传统工艺品产业的发展既是技艺类“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也推动了它们的利用,让其经济价值得以实现。该法第一条规定:“支持在一定地区内主要用传统技术、技法等制造的传统工艺品。振兴传统工艺品产业,有利于国民的生活富裕,能对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
”传统工艺品产业的管理是由日本经济产业省负责,这与文化财的管理由日本文化厅负责不同,其一项重要工作是指定“传统工艺品”,其指定标准与“无形文化财”的指定标准有较多重合。至2015年,日本一共有 222 项工艺品被指定为“传统工艺品”,而较多工艺品的生产技术也被指定为“无形文化财”。公益法人“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协会”也依据《传产法》随之成立,其工作重点是人才的确保和培养、产品的展示和推广、产业的调查以及产业信息的提供。从 1984 年开始,每年 11 月定为“传统工艺品月”,在此期间日本各地都有普及推广活动,并举办传统工艺品月日本大会,以展示传统工艺品、推动民众体验工艺品制作。
但是,随着与传统工艺品密切联系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不断增长,日本传统工艺品的生产一直处于萎缩状态,从业人员数从 1979 年的 28.8 万人,减少到 2000 年的11.5万人,至 2012 年只有 7.0 万人。2010 年,作为日本政府“新成长战略”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促进日本对外文化贸易的“Cool Japan”战略开始实施,传统工艺品的海外市场拓展,以工艺技术的展示和体验促进旅游业发展等项目得到更大的支持。
(三)民俗类“非遗”的扩大利用
1992 年,日本颁布的《关于活用地域传统艺能等资源、实施各种活动以振兴旅游业及特定地域工商业的法律》(以下简称《庙会法》)明确了民俗艺能、风俗习惯等“无形民俗文化财”利用范围的扩大。其目的是推进日本各地区通过利用反映地方固有历史以及文化传统的民俗艺能、风俗习惯等资源,举办各种定期活动,如民俗艺能等的演出、所使用服装和器具的展示、相关主题活动,从而增强对日本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振兴地区旅游业以及相关服饰、器具等制品的零售、批发和制造。
日本文化财保护专家和民俗学者对这种利用模式最初持反对态度,如民俗音乐学者小岛美子曾警告:“民俗艺能的旅游开发不仅对音乐和戏剧而且对整个民俗文化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社区的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少的民众有时间和兴趣去参与传统节日和民俗艺能表演,因此保护与利用“无形民俗文化财”的方式不可避免地需要改变。这种地域传统艺能等资源的旅游化利用,能够让日本民众更广泛地接触这些资源,提高其认知度,并且可以增强社区成员的身份意识,推动地区振兴。1994 年,日本文化厅发布报告《时代变化对应的文化财保护对策的改善和充实》,在遗产保护的框架下肯定了这种利用模式的现实意义。
为推进《庙会法》的实施,日本一般财团法人“地域传统艺能活用中心”随之成立,并从 1993 年开始,每年在不同地点举办“地域传统艺能(日本)全国大会”。它与“(日本)全国民俗艺能大会”的不同在于不要求保持艺能演出的原生态,而是运用各种音乐、灯光、布景等增强观赏性,并同时开展户外以及相关制品的展示和交易活动。
(四)“非遗”在促进地区振兴等方面的利用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全球范围内文化艺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强,2001 年日本颁布《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根据此基本法日本文化厅从 2002 年开始制定了 4 次《关于文化艺术振兴的基本方针》。这 4 次基本方针反映出对非遗利用范围的逐步拓宽态势。2002 年的第 1 次方针对“非遗”的政策仍主要集中在传承和公开活用。2007年的第 2 次方针引入了“文化艺术立国”的理念,把“文化力”认作一种国力,以推动国家发展并且 65增强地方精神。2011 年的第 3 次方针和 2015 年的第 4 次方针把文化艺术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资源,对“非遗”的利用范围全面拓宽,扩展到推动地区振兴、旅游业发展等经济发展方面。其中,第 3 次方针的“重点战略 5:文化艺术在地区振兴、旅游业发展等方面的活用”的第一条对策指出,“不仅需要考虑恰当地传承有形和无形文化艺术资源的价值,还需要努力促进这些资源在地区振兴、旅游业发展等方面的活用”,此次方针同时提出“历史文化基本构想”下包含非遗在内的文化财综合利用模式。第 4 次方针指出文化艺术资源是推进地方创生的起爆剂,并正式把文化财的两类利用——公开活用和促进地区振兴等方面的活用合并到一起,放入同一条对策(重点战略3),同时提出通过“日本遗产”的认定,推进地方“文化财群”的一体化综合利用。此外,2015 年,日本《文化财综合活用战略计划》开始实施,当年日本财政预算 141 亿日元支持该计划,“历史文化基本构想”的制定和“日本遗产”的认定与推广被作为重点项目得到支持,以增强地方文化财的综合利用,促进旅游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
二、日本“非遗”利用的实践策略
在“非遗”利用总体战略的指导下,日本各地方积极实践各种策略,在维持公开活用的基础上,推进各类“非遗”资源的多样化利用。在日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中,本文选取了三个分别代表表演艺术、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以探究具体的推进策略。
(一)表演艺术:歌舞伎
作为日本三大古典戏剧之一的歌舞伎起源于17 世纪初期,最初流行于平民社会,后来几经变化,成为一种融入了对白、舞蹈、音乐的综合舞台艺术,并凭借奢华的舞台、艳丽的服饰、戏剧化的情节,成为当前日本古典戏剧中最受欢迎的剧种,1965 年被认定为日本国家“重要无形文化财”,2005 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歌舞伎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商业属性,目前除了日本国立剧场和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作为传承、展示和推广歌舞伎的全国性公共平台外,日本的企业、民间组织、演员也积极推动歌舞伎的发展,使其在利用中得以传承。
一是演艺企业和剧场积极经营歌舞伎演出,市场的力量推动着演出资源的有效利用。松竹株式会社在推动歌舞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成立于 1895 年,目前与众多歌舞伎演员签订了专属合同,已成为日本最大的经营歌舞伎演出和剧场的民营企业。在二战中,几乎所有东京和大阪的剧场都被空袭损毁,松竹株式会社在 1951年重建了歌舞伎专用剧场——歌舞伎座,标志着歌舞伎演出在日本的恢复。此后,松竹株式会社又重装了新桥演舞场、大阪松竹座、京都四条南座,把歌舞伎作为这些剧场的主要演出,并且每年开展“松竹大歌舞伎”巡演,在日本各地的不同剧场演出。松竹株式会社还创建了歌舞伎综合推广网站“歌舞伎美人”,整合发布歌舞伎的公演信息、新闻以及介绍各种相关知识。此外,歌舞伎演出的其他主要剧场还包括平成中村座、明治座、TBS 赤坂ACT 剧场、博多座等。
二是复活和修复传统舞台,促进地区社会凝聚和振兴发展。日本茨城县常陆大宫市西盐子地区,从江户时代后期开始使用组装式的旋转舞台举行歌舞伎公演,但在二战时走向衰亡。1994 年该地区全体居民结成“西盐子旋转舞台保存会”,根据保存下来的旋转舞台的道具和构件材料,历时三年复活了这个舞台。此后,该地区居民结成地方戏剧团“西若座”,每三年举行一次舞台的组装和公演,展示歌舞伎和舞蹈,成为促进地区再生的重要活动。日本香川县仲多度郡琴平町的“旧金毗罗大芝居”修建于 1835 年,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歌舞伎剧场,后因利用率不高而被废弃。1972 年琴平町开始对其移动约 300 米后(由于原址有火灾风险)修复重建,工程历时四年,其舞台装置仍保留着江户时代的人工操作模式。1985 年开始,每年春季“四国金毗罗歌舞伎大芝居”公演在此举行一个月,吸引各地的歌舞伎爱好者到访,成为地区旅游的重要资源。
三是创新剧目形式、拓宽演员工作内容,扩大歌舞伎的影响范围。为了吸引更多观众,歌舞伎演员一直在商业演出中尝试着新的表演形式。例如,第三代市川猿之助譹訛在 1986 年首创“超级歌舞伎”,它是在传统歌舞伎的基础上,融入了其他剧种的各类音乐,并借鉴西方戏剧的灯光和舞台艺术,创造出更加令人激动的场景和效果,被称为“成人的童话剧”,2015 年在全球颇受欢迎的动漫作品《海贼王》也被改编成超级歌舞伎。同时,歌舞伎演员不断拓宽自己的工作内容,如创建新的演出平台、出演现代戏剧、参加电视节目等,使歌舞伎的知名度得以提高。例如,第十八代中村勘三郎创建临时户外舞台“平成中村座”,再现江户时代歌舞伎剧场的小规模且亲近的氛围,从 2000 年开始在东京、大阪、波士顿、纽约等地都开展了公演。他也广泛涉足现代剧,以及出演多部电视剧和电影,参与多个广告和电视综艺节目。
(二)传统技艺:美浓和纸
日本岐阜县美浓市的手抄和纸技艺已有1 30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出的传统和纸不仅纤细且触感细腻,加上做工精美又耐用,成为日本代表性的和纸并被广泛使用,如用作信纸、书简修复纸、装裱衬里、窗户纸、灯笼纸等。在传统和纸生产技艺的带动下,美浓成为日本重要的和纸生产地,美浓和纸在 1985 年被日本经济产业省认定为“传统工艺品”,并且其各类和纸生产现已商标化,统一注册为“美浓和纸”。最能代表美浓和纸悠久及高超技艺的是“本美浓纸”,其在 1969 年被认定为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并与石州半纸、细川纸一同以“和纸”名义在 2014 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譺訛对美浓和纸传统生产技艺的利用呈现出全方位、广渠道的多元化格局。
一是利用美浓和纸“非遗”资源及品牌,统筹地区造纸产业发展。美浓地区的造纸产业已经形成以“非遗”为核心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本美浓纸,由本美浓纸保存会负责保护与传承这项作为“非遗”的工艺技术,只有会员能够制造出本美浓纸;第二层是美浓手抄和纸,由美浓手抄和纸合作社来推动美浓手抄和纸文化的传承、技艺的专研以及新市场的开拓;第三层是美浓和纸,由美浓和纸商标合作社推进在“美浓和纸”注册商标下,包括手抄纸和机械抄纸在内的各类和纸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第四层是全体美浓纸,由岐阜县纸业联合会来管理以美浓和纸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各种与纸相关的行业。这四个层次的生产规模逐步增大,并且形成了工艺技术的保护与利用相互依存的有效共生模式。
二是推动和纸创意性开发,拓展和纸消费市场。随着 19 世纪西方低成本机械造纸的引入以及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现代化,日本和纸的生产受到了极大冲击。二战后,美浓市的手工抄纸被机械抄纸替代的速度进一步加快,1955 年至 1985 年的30 年间,造纸产业的出货额从 9.2 亿日元增长到132.0 亿日元,但从业人员却从 2 324 名减少到1 057 名,造纸单位数从 686 个缩减到 119 个。面对生产和消费的压力,美浓和纸充分发挥其独有特性,并与现代设计相融合,不断创新产品,巩固“唯有美浓和纸才行”的市场,并开发新的市场需求。 65例如,利用和纸制作各类小配件、服饰、和伞以及艺术灯具、纸窗等室内装饰品,并且使用和纸原料制作吸油面纸、膏药等自创产品,都受到了大众消费者的欢迎。
三是举办特色灯具艺术展,提升美浓和纸知名度并推动旅游业发展。面对和纸产业以及地区经济陷入的衰退危机,“美浓和纸灯具艺术展”从1994 年开始每年秋季在美浓的传统卯建房屋街道举行。该艺术展由日本当地工商会议所、青年会议所以及居民组成的“美浓和纸灯饰艺术展实行委员会”组织实施,并有众多居民志愿者参与,每年募集和展出使用美浓和纸创作的数百个灯具作品。近年来艺术展的规模不断扩大,首次展览的举办经费大约为 120 万日元,到目前已超过 1 000万日元,其中当地补助金约占 2/3,而参观人数已从最初的四千人发展到现在的超过十万人。艺术展的举办也了传统历史街区及其周边的设施建设和振兴。艺术展及其相关措施获得了广泛认可,于 2005 年荣获总务大臣表彰的地域建设奖,并于2008 年荣获第一届 Tiffany 财团奖的传统文化大奖,获得广泛认可。
四是推动技艺的全面展示、体验和培训,促进“非遗”保护与利用的共进。建设各种博物馆展示和宣传美浓和纸,成为“非遗”资源利用的公共平台,包括展示美浓和纸历史与作品的美浓和纸会馆,展示美浓和纸灯具艺术展得奖作品的美浓和纸灯饰艺术馆,房屋障子全部利用美浓和纸制成的美浓史料馆等。这些博物馆也是销售各种美浓和纸产品以及当地特产的平台,而且还提供学习美浓和纸技艺的课程。例如,美浓和纸会馆里开设了使用正统道具和天然原料的课程,时长在 20 分钟至24 小时不等,收费在 500—3 000 日元,并且有学习证书颁发。此外,日本校园手抄和纸技艺体验课程也在开展之中。同时,本美浓纸保存会和日本政府正在规划建立利用和纸制作技艺的监控系统,以防止“非遗”资源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三)风俗习惯:壬生花田植
壬生花田植是一种通过祭祀稻神以祈求水稻丰收的传统农业仪式,其起源可追溯到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3 年),其中“花田植”乃盛大美丽的插秧活动之意,由于此仪式在广岛县北广岛町的壬生、川东地区开展而得名。该仪式在每年插秧结束后的六月第一个星期日举行,展示了牛耕田、插秧女插秧等传统生产技术,并与插秧歌、乐器伴奏等民俗艺能相结合。壬生花田植在 1976 年被日本指定为“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2011 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在极力保护原真性的同时,这项仪式一直被日本作为一种文化旅游资源利用着。
一是利用传统仪式吸引游客,促进地方振兴。作为一个每平方千米仅有 29.3 人的山地地区,北广岛町的人口数一直处于减少状态,第三产业已替代农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花田植、民俗艺能等传统文化被作为旅游资源得以重点开发,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壬生花田植是北广岛町目前三个(另有大花田植、原东大花田植)尚在开展的花田植中最知名的一个,每年仪式当日会吸引一万多名游客前来观赏。仪式与当地民俗艺能充分结合、共同推广,主要包括三种活动:仪式中各团体的、花田植仪式会场的公演、神乐会场的神乐表演。前两种活动涉及壬生花田植作为“非遗”的内容,保持着传统仪式的原真性,同时加入了当地花笠舞蹈等民俗艺能表演,游人可以免费参与。后一种活动则需要购票入场,观赏北广岛町代表性神乐表演。这三种活动相距 1 公里内,且在时间上接连进行,以方便游客观赏。
二是开展各地公演、成立少年田乐团、建设展示馆、推广仪式和相关艺能。壬生花田植的指定保护团体“壬生花田植保存会”每年都组织壬生和川东两大田乐团参加广岛县内外的各种活动,表演壬生花田植的音乐和歌曲,例如 2013 年至 2014年两年间共参演 7 场活动,并且早在 1987 年,壬生田乐团就走出了日本,参加了美国著名的史密森尼民俗生活节(Smithsonian Folklife Festival),尽可能地展演了壬生花田植仪式的原貌。壬生花田植保存会还组织当地的小学成立壬生少年田乐团,向学生传授花田植的音乐和歌曲,并在年度仪式当日让少年田乐团参与演出。此外,位于花田植仪式会场附近的“芸北民俗艺能保存传承馆”成为一个长期且固定的推广和展示北广岛町“无形民俗文化财”的空间,吸引游客参观。
三是建立“壬生花田植认证商品”机制,完善地方特产的品牌建设。壬生花田植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后,为了增强北广岛町当地特产的竞争力,“壬生花田植特产品牌认证委员会”成立,代表北广岛町政府部门、观光协会和工商会,专门负责认证当地食品、生活用品等特产作为“壬生花田植认证商品”,通过统一的认证标志推广商品,并重点在销售促进、特产开发、旅游开发三个方面推进特产的品牌化建设。至 2014 年,一共有 26 个单位的 66 种商品获得认证,涉及酱油、味噌、羊羹、煎饼、茶叶、饼干、辣椒、香菇、果酱、一笔笺、灯笼、斗笠等多种商品。同时,认证商品的一部分销售收入捐献给壬生花田植保存会,以支持花田植的保护与传承活动。
三、日本“非遗”利用的经验与启示
根据日本近七十年的“非遗”利用实践,本文从“非遗”资源的利用程度、利用策略、利用管理、利用趋势四个方面,总结日本实践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利用程度逐步加深,保护与利用相互促进
日本近七十年来对“非遗”的利用程度呈现出明显的逐步加深的演变过程:从最初的简单公开活用,到加强最容易利用项目——技艺的利用;再到推动民俗艺能、风俗习惯的利用;最后到目前把“非遗”利用与地方振兴广泛结合起来。虽然中国对“非遗”的认识起步较晚,但是实践过程与日本有相似之处,起初也仅注重对“非遗”的保护,特别是对濒临失传项目的抢救。在“非遗”保护政策体系和有效传承机制基本建立后,中国也开始推动“非遗”的合理利用,以实现其经济价值,并通过利用促进保护与传承。2012 年,中国“生产性保护”概念的提出使得对“非遗”资源的利用进入更加规范的阶段。这种演变过程具有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它既与“非遗”资源自身的利用难易程度有关,涉及项目的类别(例如技艺和知识类项目最容易被利用)、传承发展情况、社会认知度等影响因素,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例如地区或乡村振兴需要加大对“非遗”资源的利用)。中国与日本一样,也经历了遗产保护专家、民俗学者等对过度利用的担忧,但是日本的实践结果表明,只要利用策略得当,管理规范,对“非遗”的保护与利用是可以共生且相互促进的。因此,中国应当坚定、有序地推进“非遗”的合理利用,不断优化利用模式。
(二)利用策略根据项目的差异各具特点
日本根据“非遗”项目自身特点制定利用策略,不同种类项目的利用策略不尽相同。对于表演艺术,利用的重点是推进演出数量和受众范围的增加,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对演出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日本国有、民营、社区等多类剧场的建设和公演,并在有效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剧目和拓宽演员工作内容,提高表演艺术的影响力。此外,地区表演舞台的建设也是促进地方振兴的较好途径。对于传统技艺,利用策略更为多元化,在支持特定个人或团体传承核心技艺的基础上,推动相关衍生产品的创新开发,促成以“非遗”技艺为核心的产业链整体发展,并重点推进产品展示、技艺体验、教育培训等活动的开展,带动地区旅游业发展。对于风俗习惯,利用的重点是推进生产、生活、祭祀等仪式以及传统节庆活动的开展,并与地区民俗艺能公演、民俗文化展示、特产推广售卖等活动相结合,推动以旅游业为基础的地区工商业的全面发展。由此可见“,非遗”资源的利用策略需要根据“非遗”项目的自身特点来制定,目前中国把“非遗”项目划分为十大类,有传统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也有传统美术、技艺、医药等技艺和知识,还有民俗、传统体育游艺等风俗习惯,对不同的项目需要借鉴和制定不同的利用策略,并充分结合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
(三)利用管理依靠多部门、多主体共同推进
虽然日本的“非遗”的保护是由其文部科学省的文化厅负责,但是对于“非遗”的利用,日本多个政府部门都在积极参与。例如,日本传统工艺品产业的管理由其经济产业省负责,而民俗艺能、风俗习惯等的利用由国土交通、经济产业、农林水产、文部科学、总务等部门协调推进。1994 年,日本文化厅报告《时代变化对应的文化财保护对策的改善和充实》明确提出“文化财行政部门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要努力谋求与规划、旅游、工商、农林水产以及建设等关联行政部门的适当合作”。同时,日本对“非遗”资源的利用特别重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这与日本的文化艺术基本方针是一致的,“明确个人、NPO 和 NGO 等民间团体、企业、地方公共团体、国家等各个主体所担当的角色,谋求相互间更强有力的合作”譺訛。中国对“非遗”的保护与利用都由文化部门负责,但是由于文化部门工作重心在保护,而“非遗”的利用又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部门,因此中国整体上对“非遗”利用的管理不够深入、缺少着力点。在目前文化、旅游管理部门合并的背景下,亟须建立多部门协调配合、共同推进“非遗”利用的管理体制。此外,民间团体、社区等多元主体在中国的“非遗”保护与利用中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造成目前对在政府和企业推进下“非遗”资源过度利用的担忧。
(四)利用趋势为文化遗产的一体化综合利用
从《文化财保》颁布至今,日本对“非遗”的保护与利用都是与物质文化遗产在同一制度框架下开展。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开始推进文化遗产的综合利用,鼓励各地区对聚集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体化开发利用,主要项目包括制定“历史文化基本构想”和认定“日本遗产”,并成为日本“非遗”资源利用的趋势。例如,“日本遗产”认定的是展现地区独一无二历史和传统的遗产故事,这些遗产故事串联起甲胄、寺院、神社、城郭、遗迹、传统艺能等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在国内外推广这些故事来展示各地区的魅力,从而促进地区文化遗产群的利用。2015 年至2017 年共认定三批 54 项“日本遗产”,计划到2020年认定 100 项。目前,中国对“非遗”资源的利用模式还较为单一,通常只考虑某单一项目,缺少对地区文化遗产利用的整体把握,可借鉴日本对地区文化遗产的统一管理和一体化利用模式,把对“非遗”的利用纳入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整体框架中,充分挖掘“非遗”资源与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契合点,通过推广地区文化魅力来促成“非遗”资源的综合利用。
结 语
目前,中国对“非遗”的利用正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日本对“非遗”的利用经验能够回答中国“非遗”利用中尚未解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对于哪些“非遗”资源可以加大利用力度,应当依据“非遗”资源利用程度演变的客观规律,剖析影响利用难易的各种因素,评估“非遗”资源的利用效益,率先推进难度小、效益好、收益面广的“非遗”利用项目,重点扶持对地区振兴有较好影响的项目,逐步扩展利用范围、加深利用程度。对于哪些方式可以用于“非遗”资源的合理利用,应当根据“非遗”项目自身特点,对不同种类的项目,采取差异化的利用方式,并把对“非遗”的利用纳入文化遗产的一体化综合利用模式,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充分融合。对于哪些管理机制可以推动“非遗”资源的有效利用,应当把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推进“非遗”保护与利用的多部门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性,形成共同推进“非遗”利用的合力,这是实现“非遗”合理利用的必由之路。
虽然日本“非遗”利用实践展现的规律性经验对于中国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是起步较晚的中国“非遗”保护与利用工作却处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革时期,日本的“非遗”利用可以在七十年中逐步从公开活用走向促进地区振兴,而中国却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同时解决多个阶段的不同问题。这需要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立足国情,以“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尊重“非遗”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实现非遗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赢。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8年 第5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欢迎个人转载,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发送微信留言,或与我们联系,取得授权。
订阅方式
● 可以通过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8-58,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5-1052/J,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3-2568。
● 可以汇款至广西南宁市思贤路38号 民族艺术杂志社订阅,请注明订阅期数。
● 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微信公众号识别二维码订阅。
投稿方式
● 投稿邮箱:
minzuyishu001@126.com
● 联系电话:0771-5621053
● 地址:广西南宁思贤路38号 民族艺术杂志社
● 邮编:530022
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本站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站将会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E-mail:975644476@qq.com
本文链接:http://chink.83seo.com/news/7281.html
上一篇
申请注册商标费用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