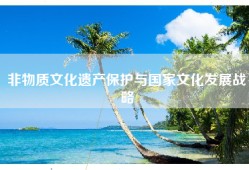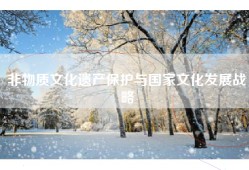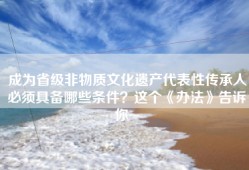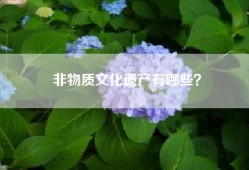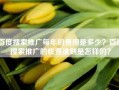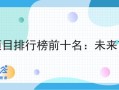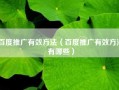景德镇城市形成的历史阶段及其非物质文化特点
- 资讯
- 2025-03-15
- 61
景德镇城市形成的过程漫长而曲折,其街道里弄作为景德镇区域文化的象征,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印记了千百年来景德镇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历史足迹,反映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请看徐桃生的《古代景德镇城市形成及城市文化特点》---
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景德镇是国家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1800多年的制瓷历程中以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技艺精湛、品质精良、体系完备、影响深远而著称于世,以集大成者的英姿体现了中国陶瓷的卓越成就,声名远播寰宇。景德镇由瓷器形成瓷业,以瓷业铸就瓷都的城市兴起与发展历程,成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靠单一陶瓷产业勃兴的“手工产业典范,创意产品先驱”城市。
景德镇城市形成的历史阶段
城市起源有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两种:因“城”而“市”就是城市的形成先有城后有市,市是在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市”而“城”则是由于市的发展而形成城市,即先有市场后有城市的形成。
古代景德镇作为一座单一手工业城市,“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其城市形态“沿河建窑、沿窑成市”特色鲜明。伴随陶瓷产业的壮大,商业的贸易兴盛,城市人口日渐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功能日臻完善,形成“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的陶业都会,则是因“业”而“市”,因“市”而“城”。
其城市形成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乡村、市镇、城市三个阶段。
两汉、两晋:农工不分乡村时期。
根据考古资料证实,浮梁(景德镇)早在商周时期,境内就有先民烧制陶器。然而,关于浮梁(景德镇)是何时开始烧造瓷器的问题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但据《浮梁县志》载“新平治陶,始于汉世”和清代《南窑笔记》“新平之景德镇,在昌江之南,其治陶始于季汉”的记载,结合2016年浮梁东流燕窝里一座东汉熹平五年(176年)墓出土的2件青瓷罐分析,景德镇东汉晚期开始由制陶向制瓷转化。如果按《南窑笔记》说法将西汉和东汉划分为“伯、仲、叔、季”四个阶段的话,“季汉”属于东汉晚期,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成熟陶瓷诞生的时期。
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江州之乱”,陶侃平江东寇,设“新平镇”于昌江之南,这时浮梁(景德镇)地区虽然有了名称,但还属江州鄱阳郡治下,并无行政建置,“新平镇”只是军事意义上的“镇守”,《新唐书·兵志》中说:“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既然有驻军,就要有后勤供应,部分散居于乡间村落的人们随之而来,在交通要道或临河开阔地形成新的聚居区,从事集市贸易,集镇也就自然形成。“东晋时,徐姓商人住此经商,后发展为商业区,故名徐家街”。
唐、宋、元:产业功能市镇时期。
据《景德镇陶录》记载:景德镇“水土宜陶,陈以来土人多业此”。南北朝时期的连年战乱在加剧人口迁徙频率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地域的交流往来,间接了经济的发展,偏于一隅的浮梁(景德镇)借以相对安宁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发展迅速。
唐武德四年(621年)析鄱阳置新平县,县治在现在的浮梁县北部江村乡沽演村一带,成为浮梁(景德镇)治域的开始,经废并复设在天宝元年(742年)更名浮梁县。
整个唐代,浮梁(景德镇)的优势产业一是茶叶,有敦煌遗书之《茶酒论》“浮梁歙州,万国来求”和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记载描述;二是瓷业,有陶玉载瓷入关中称“假玉器”、霍窑“体稍薄,色素润,佳者莹缜如玉”的美名。景德镇作为浮梁县治域下的市镇被称为“昌南镇”、“陶阳镇”,这时的城市类型还属于小市镇。
宋代人汪肩吾在《昌江风土记》描述到:“(这里的人们)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湘、吴、越间,为国家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时期浮梁(景德镇)的产业类型和经济状况。宋代,景德镇陶瓷产业兴盛,商品经济发达,以“青白瓷”跻身全国名窑行列,并形成一个庞大的“青白瓷窑系”,影响达十余省窑口。行销如南宋蒋祈《陶记》记载:“若夫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此川、广、荆、湘之所利……此江、浙、福建之所利,必地有择焉者。”
生产规模的庞大,行销地的广博,必然带来丰厚的利润,税收收入也就自然高涨。据《宋史·食货志下八》记载:“宋熙宁十年(1077年)景德镇的商税达到了3337贯950文,与同年定窑所在地曲阳龙泉镇商税为359贯480文比较翻了近十倍。”可见其陶瓷产业规模的庞大。现有的考古调查资料也显示,宋代瓷窑遗址主要分布于景德镇老城区和南河流域,其数量有100余处。因此,《宋会要辑稿·方域》中记载的“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景德镇设“镇”建制并以宋真宗“景德”年号命名,并不是孤立偶然的,完全应对了宋代高承所著《事物纪原》卷七《库务职局》中“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的条件。
也正是因为陶瓷产业规模的庞大,陶瓷手工业生产从农业生产分离出来,出现了专业制瓷作坊。这个时候开始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优势产业的集中就显得越来越有必要,于是分散在乡间村落里的家庭式作坊逐渐向有五龙抢珠之势的“珠山”(景德镇)周围迁徙集中。然而,这个集中的过程相对缓慢,应该从唐代开始,一直到明代中期才完成。
由于产业的发展,规模的扩大,劳动力的需求也就增大,于是邻近周边的农村人口和北方因战乱南迁的工匠艺人来景德镇讨生活。从目前资料查考,外乡人迁居景德镇从事陶瓷业时间最早在南宋绍兴年间。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景德镇所辖三洲一镇为6.1万人,到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居民达12.1万余人,咸淳五年(1269年)增至13.7万人,到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又猛增到19.2万人,仅30余年就增加了40.2%。
大量人口来到景德镇,其中不乏劳动力,绝大部分进入陶瓷产业各个主要和辅助环节中,促进了陶瓷产业内部分工逐步传统制瓷技艺。”黄国军少。现代气窑、电窑细化,为明清景德镇陶瓷产业分工明确、操作规范、链接俱全的完整瓷业体系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丛聚的外来人口因生产生活的需要,造窑、建厂、修宅使镇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
从部分族谱记载分析,南宋时期景德镇街区大致为东起十八桥、西濒昌江,南起老关帝庙(今戴家弄附近)、北至里市渡,到元代镇区已向南延伸扩展到桥一带。据《景德镇地名志》记载“相传在元代,有位状元回乡路过此桥,因马失蹄被摔下来,时人便称此地为桥”和从近年桥遗址考古发掘出15座房基遗迹显示可以印证,元代窑厂、作坊、民房、店铺、寺庙等世俗建筑沿着昌江东岸狭长的、较为平坦的坡地相继间杂兴建,形成带状城镇的雏形。
然而,宋元时期,朝廷虽然在景德镇设“监镇官”,浮梁瓷局有大使、副使,但监镇官的职责除了管理镇内治安、盗警外,有时还兼管商税及窑税,大使、副使“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可见“监镇官”和“大使、副使”的职能与行政长官(县令、县尹)是有区别的。虽然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但单一经济模式还达不到行政建制城市的层面,所以景德镇虽然建“镇”但还属非行政建制的功能型市镇。
明、清:产业功能城市时期。
明清二代,景德镇陶瓷进入到发展高峰,瓷业生产技艺娴熟、品种繁多、质地优良、规模庞大、体系相对完备。这得益于1369年明王朝在景德镇设立“陶厂”后称“御器厂”以及清代改名“御窑厂”的皇家工厂。
御器厂(御窑厂)是明、清两代专为宫廷烧造和供奉瓷器的皇家瓷厂,是中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极为精湛的官办窑厂。在长达500余年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聚”,烧造了无以计数精美绝伦的瓷器。御器厂(御窑厂)的设立是我国陶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极大地促进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同时,御器厂(御窑厂)的设立也促进了景德镇城市的发展,以御器厂(御窑厂)为代表的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一直交织贯穿于景德镇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之中。
明清时期景德镇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陶瓷手工业城镇,“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被称为“四时雷电镇”。从文献记载看,明代景德镇城区在元代基础上向东、向北有了一定的扩展,并形成许多以姓氏和地貌命名的弄巷,人口数量有了一定的增长。“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明神宗万历实录》卷四一九中记载:“本镇统辖浮梁县里仁都、长香都等居民,与饶州府所属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窑业佣工为生”;嘉靖《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记载:“大之而两京、江、浙……诸省,次之而为苏、松……诸府、州、县,瓜洲、景德镇诸镇。”可见这时的景德镇已跻身于全国著名都会之列,成为一座著名的手工业城市了。
清代镇区规模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浮梁县志》记载:“镇距城二十里,而俗与乡邑异,列肆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唐英笔下的景德镇是“景德一镇,僻处浮邑境,周袤十余里,山环水绕,中央一洲。缘瓷产其地,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靡不藉瓷资生”,“其人居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
清代景德镇形成以御窑厂为中心,北至观音阁,南至小港咀,西至三闾庙,东至里村一带的城市格局。两条主街道“前街、后街”与昌江平行,上百条小街巷纵横交错,组成以便利往来河岸码头的方格状里弄系统,奠定了近现代景德镇城市的基本形态。
明初改饶州路为饶州府,浮梁州复为县,景德镇仍然属浮梁治下。清代隶饶州府浮梁县,镇区属浮梁县兴西乡里仁都一、三、四、五图和镇市都。虽然城市格局已经形成,但与中国古代城市按功能划分的政治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军事城市这四类城市相比,景德镇似乎游离这四类城市之外,却又置身于其中。
虽然辖浮梁治下非地方的行政中心,但御器厂(御窑厂)这一封建官方手工业组织之起到的政权作用并不逊于政治城市。虽然也有商业贸易,但不以经济功能为主,只是为维系这座城市的生存而进行。虽然不以文化功能为主,但也有文化教育机构,并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的陶瓷文化。
从东晋到明清,景德镇城市形成的过程漫长而曲折,直到1926年于浮梁县析出置景德镇市,设立市行政公署及市政委员会才具备地方政府行政职能。1949年4月景德镇解放,5月成立景德镇市人民政府,1953年6月成为江西省直辖市。
景德镇这个靠单一手工业——陶瓷产业维持其发展繁荣的城市经过千百年才走完了“凤凰涅槃”的兴起之路。
景德镇城市非物质文化特点
景德镇街道里弄有“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巷、一百零八弄”之说,景德镇的城市非物质文化特点就是从这些充满情趣的街道里弄名称中显现出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习俗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等。这些名称作为景德镇区域文化的象征,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印记了千百年来景德镇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历史足迹,反映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
以姓氏命名的街道里弄反映城市的属性。
古时的景德镇是江南重镇,瓷业繁荣,贸易发达,吸引了大量的周边地区。同乡同地的外籍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集聚在一地从业、生息、繁衍,许多以姓氏冠名的街道里弄就是族群定居在地名上的体现。
外来人口迁居景德镇后族聚而居形成弄巷,如彭家弄,彭姓居于此地,后因宋中期瓷业生产发展,坯坊增多,渐渐成为弄巷;沈家祠,明初有沈姓迁入居住,沈氏在此地建立家族祠堂,后渐渐形成弄巷;陈家弄,因明朝都昌陈氏家族迁入,故名。
不同地域族群的丛聚反映出的个性。
景德镇作为一个传统手工业城市,其它各行业在陶瓷业的引领下蓬勃发展,陶瓷业也在其它各行业的辅助下茁壮成长。邻近景德镇的府、州、县的人(甚至族群)因为景德镇制瓷业的兴盛,纷纷来景德镇谋生。他们有的从业、有的卖力、有的经商,来到景德镇聚群而居、聚群而业,在求生存、谋利益、抵欺辱的境况下,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自然地把他们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本省都昌籍的“都帮”、安徽徽州府所属六县的“徽帮”,以及除都、徽两帮之外的各籍人氏的“杂帮”,形成带有明显地域风情的群体。一些带有明显地域和行业名称的街道弄巷就自然而然随之产生,如新安巷、抚州弄、饶州弄、汉阳弄、湖口弄等就是聚群而居;铁匠弄、草鞋弄、篾丝弄、花篾弄、扫帚弄等就是聚群而业,这其中的行业无不与人们日常生活和景德镇瓷业息息相关。
吉祥文化所折射出的美好愿景。
吉祥文化的产生发展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引导人们热爱生活,激发人们的智慧创造,展望无限美好的未来,并把美好愿望的词语命名为地名,表示理想的寄寓,如迎祥弄、求知弄、安全弄、太和弄、乐兴弄、东风坦、青云巷等。这些以吉祥词语命名的街道弄巷,一方面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另一方面又反映景德镇这座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
蕴含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感表达。
自然界是一个庞大复杂生态系统,以某种动物和某种植物代表人的性格中某些象征意义,参与人类社会思想情感的交流,体现了人与动、植物之间生活交流等一系列过程。动物中被人们赋予吉祥意义的如禽类中狮、虎、鹿、鹤等;植物中被人们赋予吉祥意义的花草、树木、果实等,如牛氏弄、驰马弄、狮子弄、桂花弄、桃花弄、樟树弄。
敬畏心理形成的道德规范。
祭祀是中华民族礼仪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神、祀仙和拜祖是向神灵先祖求福消灾,从本质上说是对神灵与祖先的景仰和敬重,协调人与神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传统礼俗活动仪式。
景德镇作为一个传统手工业城市,“靠天吃饭”的意念从古到今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瓷工,除了传统的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外,陶瓷行业神的祭祀崇拜习俗成为景德镇特色鲜明的地方崇拜习俗。
陶瓷行业神崇拜这一文化现象包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对师长的尊崇、对正义的褒扬、对邪恶的鞭笞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讲,景德镇瓷业崇拜习俗的本质内涵就是崇拜劳动者本身。从景德镇四王庙、药王庙、陶王庙、土地弄、祭师祠这些地名中,我们可以很好的解读陶瓷行业神崇拜习俗这一文化现象。
趣闻轶事所传递的闲情逸致。
风俗现象千差万别、种类繁多,但是也并非无所不包,大致的范围可归纳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等四个方面。作为一个城市,景德镇的社会风俗习惯并不等同划一,但趣闻逸事却是大家喜闻乐见。“斗富弄”来源于一个斗富的故事;“赛宝坦”也来源于一个斗富的传奇;“桥”相传在元代,有位状元回乡路过此桥,因马失蹄被摔,而称桥;“低头弄”源于明代末年有一陈姓抚台住在此弄,弄口有一低矮青石门坊,当其他官员骑马来拜访抚台时,进弄都要低下头来通过,故名为低头弄,等等。这些趣闻逸事深植于群体之中一代代相沿成习。
历史虽已逝去,但回首景德镇因制瓷而名扬天下的历程,她的“凤凰涅槃”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品味和咀嚼的话题。没有记忆的城市是没有历史的城市,没有历史的城市是无根的城市。对于景德镇这样一个曾经千年辉煌又志在开创崭新明天的城市而言,历史绝不仅仅意味着过去的辉煌,更昭示着光明的未来。
在城市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今天,能够唤醒我们记忆的物质和非物质的镜像在不知不觉中“合理”消失,记忆中的影像飘逝得无影无踪。梁思成先生在《拙匠随笔》中曾说过:“如果城市里千篇一律地盖同样的房子,孩子们就会哭着找不到家门。”与历史的共生与对话,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古老的城市影像可以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消失,但不能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研究景德镇的城市发展历史,目的就是留住记忆,追忆先辈踏碎岁月流光的脚印,保护城市的文脉,守护城市的灵魂。
请阅读《景德镇文化研究》第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
本网信息来自于互联网,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本站不承担此类作品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及连带责任。如若本网有任何内容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我们,本站将会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E-mail:975644476@qq.com
本文链接:http://chink.83seo.com/news/7474.html